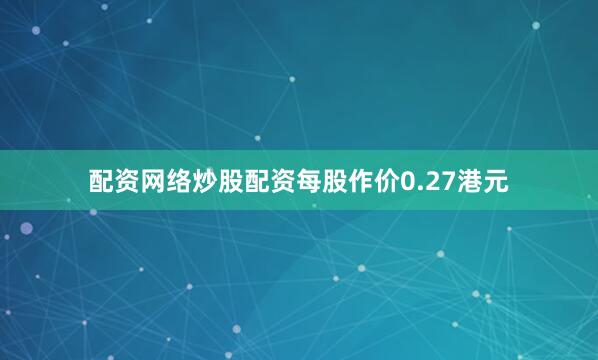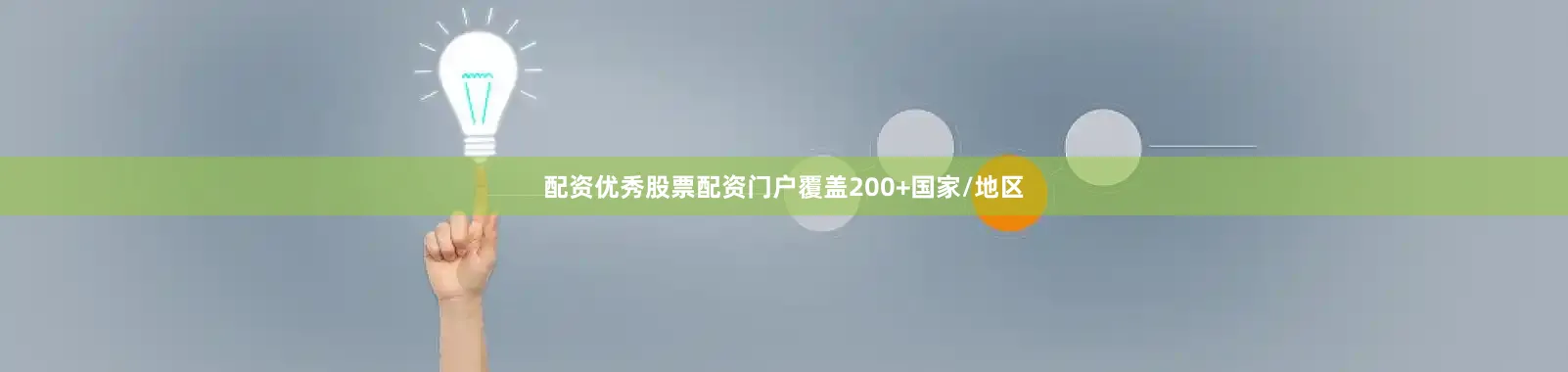公元1004年,辽国铁骑二十万如黑云压城,骤然扑向大宋腹地。宋真宗仓促披挂,亲临澶州前线。天子亲征的激励下,宋军一度在城头弩炮的呼啸中重挫辽军锐气,连辽军主帅萧挞凛也殒命于神臂弩下。
然而战场优势并未转化为胜势——宋真宗最终签下了以岁币换和平的《澶渊之盟》。后世常将此归咎于真宗怯懦,实则澶州城楼上,天子忧惧的目光并非投向城外辽营,而是频频北顾定州方向。那里驻扎着大宋十多万精锐,统帅王超却对天子八百里加急的调兵令置若罔闻。
王超手握重兵却屡屡抗命,如同一根毒刺扎在真宗心头。辽军初入宋境,他坐视其南下;澶州战事胶着,真宗多次严令其南下夹击,王超依旧按兵不动。
史书称王超“临军寡谋,拙于战斗”,被辽军声势所慑。但真宗内心的恐惧远超战场本身——六十年前后晋大将杜重威手握重兵,先是按兵不动,最终临阵倒戈,引辽军入主中原。此刻王超的沉默,在真宗眼中与杜重威的影子悄然重叠。
展开剩余61%澶州城下,宋辽双方陷入微妙的恐惧平衡。真宗忧惧王超可能的背叛,辽主耶律隆绪与萧太后同样如坐针毡:深入宋境,前有坚城难克,后有王超大军虎视眈眈,一旦腹背受敌便是灭顶之灾。
议和成为唯一出路。辽国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威望重创,宋真宗更需尽快结束这悬于刀尖的危险局面。双方在岁币数额上反复拉锯,最终三十万之数尘埃落定——它并非凭空而来,实为辽国所觊觎的关南地区年赋税额度。真宗以“代收岁赋”之名保全了领土主权,岁币支出远低于战争消耗,更可通过边境贸易回流,堪称精明的止损方案。
尘埃落定后,王超的结局堪称黑色幽默:贻误军机、抗旨不遵的他不仅未受惩处,反而加官进爵,死后更得追封鲁国公,谥号“武康”。
真宗难道不想清算?非不愿也,实不能也!辽国之所以畏惧议和,正是忌惮王超这支“引而未发”的重兵。若王超前脚“震慑”辽军退兵,后脚就被天子问罪,岂非向辽人昭告:此将根本不受天子节制?那无异于自曝软肋,诱使辽国日后在大宋君臣间施展离间。
澶渊之盟,表面是宋辽两国的城下之盟,内里却是宋真宗以巨大隐忍维持的朝局平衡术。天子在澶州城头签下的每一个字,都浸透着对肘腋之患的戒惧。所谓屈辱的岁币,竟成了避免成为第二个后晋的赎金——历史的吊诡,有时比刀光剑影更令人脊背生寒。
澶渊之盟不是战场败局, 而是帝王心术的无奈选择。发布于:湖北省股票怎么加杠杆10倍,配资网查询,百益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